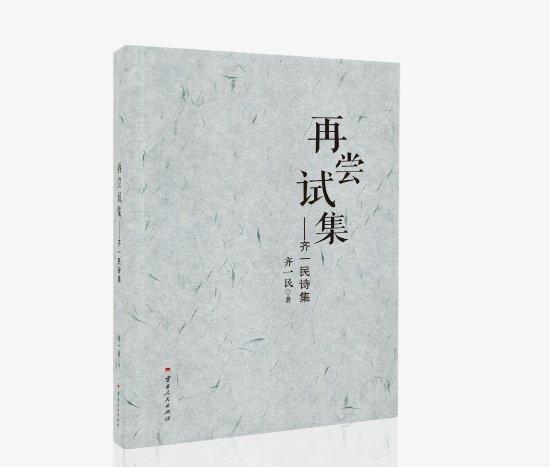
《再尝试集:齐一民诗集》,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第1版。
[摘要]
齐一民诗集《再尝试集》是其文学创作版图中一次大胆尝试,标志着这位涉猎小说、随笔、散文等多领域的“全文类作家”终于补齐诗歌领域的空白。作为首部诗集,书名化用胡适《尝试集》,既致敬文言诗、白话诗传统,又暗含对诗歌本质的当代探索。
齐一民把诗分为“诗语、诗情、诗心”三个境界。用诗的语言写诗就是诗语;因多情而发感慨是诗情;把心交给诗叫作诗心。只有同时具备诗语、诗情、诗心的诗才是一品。能写出一两首一品诗才是“大诗人”。
[对话]
何乐辉:
齐老师您好!好久没有聊天对话了,您的诗集《再尝试集》的出版给了我们一个不得不说的理由和机会。虽然现代诗歌在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但它跟小说、散文随笔比起来似乎相对小众。诗集取名《再尝试集》,很明显是对照胡适先生的《尝试集》,是对“胡适精神”的继承,我们把《再尝试集》视作《尝试集》的延续。在白话诗诞生百年后的今天,您认为这个 “再尝试” 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齐一民:
何老师好!我特别幸运地可以用和胡适先生《尝试集》雷同的《再尝试集》出版这部自己年逾六旬才成书的“处女诗集”——我特别诧异百年来诞生了那么多诗人,竟然没人想到用这个名字为自己的诗集冠名,因此说我算是个“捡漏者”。不过细想也不是,应该是命运中的一种默契和安排,因为我和胡适先生写诗的初衷其实都不是简单的写一些诗和出版一本诗集,胡适先生为可否用白话文写诗而探路,我则是出于一个小说家和“田野语言学家”的好奇心,想在用其它包括小说、随笔、对话、剧评、文论等各类文体发表作品之后再补齐最后一块“诗歌”的短板,于是,我就用一本不太丰满的诗集填补了那个空白——我是想说,我不算是一个从年轻时候就将自己定位为“诗人”的人,诗歌是我的一种研究汉语写作和扩宽文类的“道具”,是尝试了很多、不,甚至是所有其它文体(文类)写作之后的“最后一个文类的尝试”,因此我将“再”放到了“尝试”前面——它是我自己的“再尝试”,同时也是写诗的一种微小的“再尝试”。
我这部诗集分两部分,上篇是“小民诗话”,下篇才是“我的诗歌新作”,上篇能和胡适先生在《尝试集》开头写的几篇“自序”对应,都是讨论什么是诗、诗能不能这么写的,他讨论的是写白话文诗歌的可行性,我则讨论什么才是“好诗”;他解决了怎么才能写像样白话诗的问题——通过他自己的思考和创作,我呢,则在百年后现代诗的总量已经无限大的情形下,琢磨什么才是那些所谓“诗”中的“好诗”,为何它们好;他探讨的是诗的形式,我注重的则是内容,当然,我所得出的好诗要做到“三好”——诗语好、诗情好和诗心好是基于我个人感觉、是私下的尝试,但我也可以带点小骄傲地说——胡适先生的尝试是被包含在本人“三好”的头一个“好”——“诗语好”之中的,那只是好诗的头一个步骤,一定要再加上“诗情、诗心”另外两个“好”才能达到真正“好诗”的境界,而且我这个标准和尺度古今中外的诗歌甚至文学之外的艺术门类都能适用,所以说百年后我《再尝试集》的问世是一种宿命性的安排——难怪这之前从没诗人想过用这个名字冠名自己的“处女作”呢(笑语)。
何乐辉:
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出版了《尝试集》,是白话诗的开山之作,打破了文言诗的桎梏,影响巨大。胡适本人并非诗人,他曾留学美国,是最早接触西方诗的那拨人之一,在我看来,《尝试集》无非是对西方诗歌创作的引进与中国审美、意境等的中国化叙事与抒情,《尝试集》更多的是勇气。从文言诗到白话诗,的确是中国诗歌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现代诗歌(白话诗)发展至今一百年,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努力,相对比较成熟,同时也显现出停滞不前的迹象,而《再尝试集》要达到《尝试集》那种突破性和影响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功力。
齐一民:
其实我骨子里面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即使胡适先生想通过诗歌的“白话化”达到引发整体语言文字去文言化和口语化的初衷是好的、白话文运动对历史的贡献也毋庸置疑,但我还是对文言文因语言载体变革而隐退直至彻底退出表述工具选项而感到痛惜,在我早先著作《妈妈的舌头——我学习语言的心得》和我博士论文《日本言文一致问题初探》中我充分表达和论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我以为中国放弃文言文不是一种“语言变革”该有的常态,而是一种被动的突变,是一种文化上的自废武功——最理想的结局或许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并行不悖各自开花。其实在诗歌白话过程中如何保留古典文言诗的优雅和韵律一直是许多前辈诗人所关心的,比如闻一多先生就一直边写诗边思考这个问题。
说到当代诗歌的“停滞不前”是从品质上说的,但诗的产量却远超前人——更何况现在连AI也能够参与写诗、而且能写出不错的诗。如果说“停滞不前”的话可能是指诗歌和诗人早已没有百年前那些白话新诗作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所受的万人瞩目了吧——诗都没人太关注了,更何况什么是“好诗”这个问题呢?而我所尝试的就是想补救在这个问题上反思的缺失。
何乐辉:
《再尝试集》无疑是对当代诗歌困境的“突围宣言”,那么您认为当代诗歌的困境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突围?
齐一民:
“突围”算不上,只能算是“尝试突围”。
中国诗歌的所谓“困境”可能有很多,比如在AI也能写诗情形下的慌乱,比如人们对诗人的背弃甚至厌恶,或者说诗人的边缘化,等等。我觉得或者我想到的是人们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局面,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人们放弃了对“什么才是好诗”问题的思考,其实,我们的前辈——正如我前面说的,在白话文诗歌取代了几千年来通行的传统韵律诗之后,凡是那些“负责任”的诗人都边写诗边回答“什么是好诗”的问题,然后用思考的结果来衡量自己的创作,而当代诗人有这种“边写边想”习惯的人少之又少,可能因为民国时期大部分诗人都是学者出身,都有在“规则”上反思的能力,而当代“两栖诗人”为数不多,或者说当代诗人和进行诗歌理论批评建设的人是两拨人,一拨儿在写,一拨儿在评论——这和其它文学类型,比如小说随笔散文领域也差不多,结果就是诗歌总数大泛滥,真正的“好诗”、能脍炙人口、让人感动、能给与人启迪的好诗其实并不太多。
因此,我这部《再尝试集》算是“连思考带写”的特制品——因为我认为不边写边思考怎么写才好的诗人不算是一流的诗人。
何乐辉:
从《再尝试集》中我们能体会到,突围也好,变革也罢,《再尝试集》自始至终都体现出继往开来的姿态。当代诗人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齐一民:
继承肯定是继承中国古典的韵文传统,发展肯定是发展诗的新疆域。我在《再尝试集》中开篇就赞颂《诗经》,我认为或许《诗经》之后就再没超过它们的诗——超越它的简洁和文字中含有的丰富睿智。其实我从来认为文化没有时间上的“现代性”和“非现代性”之说,我认为文化价值和它们产生的时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就是说可能最早期的作品反而是顶级和顶峰,因此所谓“继承”就是不丢老的、敬畏老的,然后去创造自己时代或者具有鲜明个性的私房产品——将自己最大化的展示其实就是一种“继承”,或者说是“添加”,因为每个人作为地球之子都独一无二,都既具备现代性又同时拥有未来性。
何乐辉:
《再尝试集》中含有14篇诗论文章,从中不难看出,您对传统诗歌的喜爱,比如《诗经》,比如李白和杜甫的诗,比如朱湘的诗,又比如海子和余秀华的诗。我在想,无论诗歌创作如何变化,甚至产生不同的流派,诗歌本质性的东西是不会变化的。过去我们强调诗的意境,您在《再尝试集》中提出了诗的三个境界:诗语、诗情和诗心,大概这就是诗歌的内核与本质吧。
齐一民:
“诗语”是指诗的语言,广义来说就是诗作为一种文类的表现形式,比如是古体格律诗还是现代白话自由诗等;“诗情”的“情”是指人类的情感,比如情绪、情愫、感情、激情热情,还有最重要的“真情”等等;“诗心”的“心”是统摄人类情感的背后的本体、本质或者本性,是和“人心”相关联的一切,比如良心、爱心、善心、德性等等。“诗语”是诗的载体、是工具性的,是“无机”的和无目的性的,是符号,所有和诗形式相关的载体都包括在内,就是用什么语言(中外文)和方式(格律非格律等)写诗,后两个呢——“诗情”和“诗心”则是“有机”的,有血有肉的——“心”是肉长的,“人情”只有人类才有,但凡好的诗歌——古今中外全包,都一定会同时在诗语、诗情和诗心三个方面全部达标,缺少一项或者哪一项太弱都不可。
其实,我的这种“语、情、心”三境界论可以用于衡量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作品(小说散文随笔等)和其它艺术作品的品相,比如美术、音乐、影视作品等,因为所有艺术品都需要表现的形式(材料),小说用的是长篇的文字,绘画和书法使用的是颜料和水墨,音乐使用的是音符·······,它们的最终成果如果在形式、感情、德性三方面欠缺哪个,就都不会是最佳和最受人们欢迎的,也不会在历史长河中被保留和传递下去。
让我用《红楼梦》为例说明我的“三境界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所以被“公认”说不是曹雪芹亲笔之所,就是不仅所用语言和语感和前八十回不同,而且缺乏前面的“真情”和“真心”——倘若压根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那“情”和那“心”怎么有、怎么会同样呢?
细想其实“语”、“情”、“心”三者是互为表里和因果的,没有善心和浓情就绝不会有笔下情趣和格调,那书中的“语”——行文就自然不会有神,因此别人一读就会露馅儿,就会感觉《红楼梦》后四十回如同嚼蜡。
“心”是决定所有艺术品价值的根本——历史上那些人品上有瑕疵的作家艺术家甭管在形式(“语”)上多么娴熟、老练,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在情感和最内心深处被读者(欣赏者)全盘接受和由衷热爱。
而我们今天“诗歌界”和其它门类艺术——小说等文学作品、绘画和影视等面临最大的窘境——“语”(文艺形式)姑且不论,缺乏的可能就是后两者——真情和真心——情深意切的情和磅礴无边的爱心。
何乐辉:
如上所述,诗歌有它的内核与本质,那么诗歌有边界吗?诗歌的边界在哪里?这种边界或许是形式上的,有没有可能突破其内核与本质?
齐一民:
自从人们开始用口语白话文写诗之后——这个运动是全世界范围的,西方早已经不再以十四行诗(商籁体)作为必须的格式,东方的中国以及我们周边的亚洲国家——比如我比较熟悉的日本,白话诗歌早已成为最普及的诗歌形式,因而已经没什么形式上的限制——甚至连押韵都被认为多余,那么可以说就是无限和无边际的了,既然没规矩,就没什么可“突破”的了。
至于诗歌的“内核”和“本质”,我的体会就是用最讲究、最简洁和最集成化的语言表达人类最强烈炙热的情感。
人类的情感是人独有的,把它表达出来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本能,这一点会恒久不变,表达的方式可以是绘画和音乐,当然也可以用“有韵味的长短句”——诗歌来表达了。
何乐辉:
您认为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是什么?
齐一民:
用最简略的话说,就是它的存在证明人还是一种有高贵感情并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动物。
何乐辉:
上面我们谈了诗歌的特质、现代诗歌的困境与突围路径。作为作者,请您谈谈您的诗作与当代诗歌有哪些不同之处。在创作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齐一民:
我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是在写作三十年、出版过七百多万字其它文类作品之后才出版第三十五部作品——诗集的,如果将诗歌作为文学最高级殿堂的话,那么我是从底下一步步爬上来的——踩着其它文类、比如小说散文和对话等的台阶,而绝大部分“专业诗人”头一部书就是诗集,而且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诗集。
正因为我不把“诗人”作为自己的定位,诗歌属于创造中的“边角废料”,因此我这部诗集里的几十首诗是我在过去二十年中一首首“攒”起来的,我从来不想每天写诗或者只写诗,我仅把这种长短句交叉的文体当做所有文体(文类)中的一种工具,比如它像是个短刀短枪,而各种长短不一的小说文体则是长枪短炮,当有压抑不住不吐不快的情感想表达时,哪种顺手我就使用哪种,正所谓文学有十八般武艺,诗歌只是其中之一。
那么做的好处是我能确保笔下所有的诗都是真情流露的结果——人不可能每天每时刻都情绪高扬、都写诗,那种诗是“挤”和“憋”出来的,即使“诗语”——形式上像是诗,但绝不会有饱满真挚的“诗情”、更不要论“诗心”。
我要保证自己所有的诗都是生命的精髓。
总之,我喜欢让自己保持在“非专业诗人”和“旁观者”的自在状态,因为我一贯主张凡艺术均属于“游于艺”的范畴,出最佳成果的前提是始终深处局外、始终随心所欲、始终身处不为任何名号制约的状态。
另外,我也想通过出版一部诗集证明: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其实写诗并不太难——只要你有广义的诗心和诗意,你热爱生活,你喜欢用语言记录生活,相反,可能那些诗人想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会有技术上的不适。写小说的技能不仅包括语言的灵活把握和想象力上面的过人,还要有整体布局的心机,这些都可以应用到写诗上面,只是换一种方式和举手之劳而已。
诗心和诗意——对生活的热爱之心和表达的强烈意愿在所有艺术门类都是一样的,根本不该有太多死性的门槛、圈子甚至门阀。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用各类文体甚至所有(文类)表达自己生活经历和记述世态炎凉的文化人——当然,这就不能单单没有写诗的本事。
《再尝试集》的问世为我做了证明,也是我三十年写作长途跋涉历程中的一个“收文体全红”的里程碑,是收官时刻。
何乐辉:
您的诗歌语言既有古典韵味,又充满现代性,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齐一民:
那是我的追求、也是民国时期的大诗人们比如朱湘、闻一多的追求,闻一多先生的“三美”——声美、意美和形美,就将中国古典诗歌诗词的古雅包含在内。
我认为最好的白话诗歌一定要努力把中国自从有文字之时起始的所有长处都包括进去,既然有为何不用呢?因此我不喜欢那些所谓的“纯口语诗”——既然说话就行,何必把那些平凡的句子叫做“诗歌”呢?
诗歌毕竟是高于平凡话术的一种艺术,一定的优雅总是该有的。
何乐辉:
在《也说叙事诗》一文中,您批判了当代诗歌的 “非诗化” 倾向,比如您提到了北岛的“生活:网”。那么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回归诗歌最原始的叙事与抒情功能的呢?
齐一民:
也可能我批评错了,单单一个“网”字肯定是北岛作为诗人的行为艺术,但假如“网”是其它诗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诗的一部分了。
批评“非诗化”的前提是说明什么是“好诗”,我用“三个境界”来判断什么是诗和好诗,就可以将那些不是好诗甚至不是诗的文字给清除出去。
何乐辉:
您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在选取题材时,您遵循怎样的原则?
齐一民:
“有最真切情感而发”是我写诗的大前提,选材之所以多可能是由于我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比常人要多——我从事过很多不同行业的工作,那些经历是它们(诗)产生的平台。
何乐辉:
《再尝试集》中有没有您特别钟爱的作品?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吗?
齐一民:
我最满意的诗是那首“墓地归来的感受”——我说自己未来的墓地就是遍布全国图书馆书架上自己留存下来的几十部作品,凡去翻看我作品的读者就都是为我扫墓的人。
那是我最真挚的“世间留言”。
何乐辉:
在 AI 时代,人类诗歌创作面临挑战,有人提出了人机协作的创作构想。您认为诗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人该如何坚守自己的阵地?
齐一民:
说到AI写的诗,用我的“三境界说”就能判读它写的是不是好诗呀——首先,从“诗语”上说那些作品绝对算是诗歌,而且还是不错的、经过千锤百炼和广集众长的诗歌,然而它有“诗情”吗?没有吧,或许有一点点,至于“诗心”——它不是人,是冰冷的电脑部件,所以没有“人心”,更甭说“热心”——人心可是肉长的,“真心”和“良心”“爱心”只有大写的活人才拥有。
感谢何老师的访谈!
[附录]
(一)图书简介
齐一民诗集《再尝试集》是其文学创作版图中一次大胆尝试,标志着这位涉猎小说、随笔、散文等多领域的“全文类作家”终于补齐诗歌领域的空白。作为首部诗集,书名化用胡适《尝试集》,既致敬白话诗传统,又暗含对诗歌本质的当代探索。
诗集以“诗论+诗作”的独特结构展开,齐一民通过大量研读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理论,构建起个人“诗之网”作为创作基石。他突破传统抒情范式,借鉴《孔雀东南飞》的叙事传统,将街头见闻、人际感悟与时代命题熔铸于诗行,语言灵动跳脱,时而诙谐幽默如“驴粪蛋般黝黑和华丽”的比喻,时而深沉内敛直击人心。这种“用词语酿酒”的创作理念,让日常琐碎升华为诗意存在,如他笔下的《诗经》式变奏,在稳当结构中展现语言韵律的千变万化。
作为一部诗歌实验性作品,《再尝试集》不仅完成对“什么是诗”的自我叩问,更以叙事诗为载体记录时代褶皱中的个体生命体验。那些“不啻为公元20××年日记”的诗篇,既是对消费主义浪潮的隐喻式批判,亦是对人性微光的深情凝视,恰如“星河里的微光”,为当代诗坛点亮一盏兼具先锋性与烟火气的明灯。
(二)对话者简介
齐一民:
齐一民,笔名齐天大,“全文类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客座讲师。1962年生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1984年)、加拿大蒙特利大学公共管理硕士(199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2013年)。齐一民自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出版作品35部,计700余万字,包括《马桶三部曲》《雕刻不朽时光》《妈妈的舌头》《我与母老虎的对话》《我的名字不叫“等”》《六十才终于耳顺》《百剧宴》《再尝试集》等。其中《总统牌马桶》等在国外出版。
何乐辉:
何乐辉,北京华卷文化中心创始人,资深出版观察人,在传媒出版界从业二十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