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格丽特·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与个性的作家、电影编剧、导演、戏剧家。1984年,小说《情人》夺得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杜拉斯因此蜚声国际文坛,成为20世纪的符号。
她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十多部剧本。时至今日,许多读者依旧通过《情人》认识杜拉斯,也正因为《情人》的知名度,使得人们看待她的眼光“非常狭隘”。在获奖之后,杜拉斯就发现自己正在被通俗化,以至于在后来某一个时期,她本人甚至不愿谈起《情人》。
《情人》是其一生的高度,却不足以概括她的写作成就。在一次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杜拉斯曾说:“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她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她认为,除了写作之外,她已一无所有。
当杜拉斯谈论杜拉斯时,她在谈论些什么?
本文节选自《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11月,译者缪咏华)。在其中,杜拉斯谈及了她的写作历程,讲述了《情人》及其之外,一个更加丰盈饱满的写作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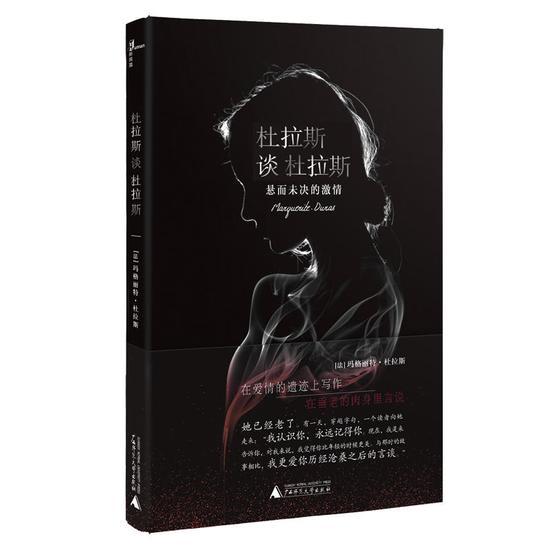
《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 悬而未决的激情》
促使你从事写作的原因?
我感受到需要在白纸上重建某样东西的急迫性,却没有力量完全做到。那个年代,我大量阅读,而且不可避免的,写作的急迫性是如此强烈,乃至于我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受到什么影响。作家得等到第二本书的时候,才会看清楚自己的写作方向,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慢慢摆脱对自己从事文学这一念头的迷惑。
怎么开始的呢?
我十一岁时住在交趾支那,每天就算在树荫下也有三十度高温。我写了好几首诗——每个作家都是从写诗开始——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根本就一无所知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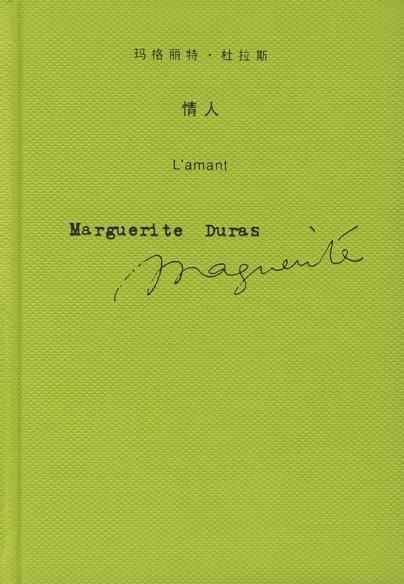
《情人》
写《情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某种快乐。这本书走出晦暗——我将自己的童年流放进去了的晦暗,而且它毫无规则可言。一连串彼此没有关联的片断,我找到了也放弃了的片断,但我不曾在此停留,既没有宣告它们的到来,也没有帮它们作出结论。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说出这段你自己都定义为不可告人的故事呢?
我摆脱了疾病、疲劳,这给了我渴望,让我想在这么长的时间后重新回头审视我自己。跟灵感无关,我比较会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感觉。《情人》是个野蛮的文本:而我身上这粗暴的一面,则是透过扬·安德烈亚的《M.D。》一书,才发现的。
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符合实际情形吗?
这么些年,这么多往事,我八成撒过谎。当时母亲还活着,我不希望她发现某些事。然后,有一天,她过世了,剩我一个人,我就想:现在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情人》里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服装、我母亲的愤怒、她让我们咽下去的淡而无味的食物、中国情人的豪华房车。
就连他给你钱也是真的?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找个亿万富翁,把他送给我家。他送我礼物,我们搭车兜风,他还请我们全家上西贡最贵的餐厅。席间,没有人跟他讲半句话,殖民地的白人有点种族歧视,我家人说他们讨厌他。当然,只要涉及金钱,家人就视若无睹。好歹我们不用卖掉或典当家具来求温饱了。
你对这个男人还留有什么其他的记忆?
我不喜欢他那中国人的身体,但我的身体却让他有快感。这种事,我还是到了那时候才发现的。
你指的是欲望的力量吗?
对,彻彻底底,超越感情,不具人性,盲目。没办法形容。我爱这个男人对我的爱,还有那情欲,每次都被我们俩天差地远的歧义所燃烧。
《情人》一书光在法国就卖了一百五十万本,还被翻译成二十六国语言。这本书如此畅销,你怎么解释?
原本我的编辑热罗姆·兰东才印了五千本!几天就销售一空。一个月内加印了两万本,于是我就不担心了。我把这本书搁在一边,没再打开过,我一直都这么做。有人对我说过:爱,是保证成功的主题。
可我写《情人》时想的并不是爱。我甚至还想用这些反正我已经处理过的主题来让读者感到无聊,激怒他们。我重拾这些故事,万万没想到大家竟然会把它当成一本通俗小说来看。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令这本书大卖呢?
这本书,我认为,传递出了我每天因为写作十个钟头而享有的极大乐趣。通常法国文学都搞混了,误以为严肃认真的书就会很无聊。其实,读者之所以看不下去自己正在看的书,是因为这些书都自负得不得了,充斥着想反映出别样东西的愚蠢自负……
你知道你如今已誉满全球,因为这件事——有时候就光因为一件事——写了《情人》?
终于,大家再也不能说杜拉斯只会写些“理性的玩意儿”……
你会想指出如何去诠释《情人》一书中某些点的关键吗?
这是一本小说,就这样。谁想引导它,谁就哪儿都去不了。故事还没结束,仅仅是书停了下来而已。爱,快感,这些不是“故事”。至于另外一种阅读方式,较为深入的阅读,即使真的有,也不会出现。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去领会它。
你认为从《情人》起,你最彻底的风格变化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的写作一直都一样。在《情人》里,顶多说一句,我随意发挥,无所畏惧。现在人们比较不怕——最起码外表看起来不怕——自己会前后不一致。
从《情人》开始,你的书写越来越轻盈。
跟从前相比,是说话的声音改变了,就像是某样东西不由自主地就变得简单。
请你解释得更清楚一点。
《情人》是一本满溢文学气息的书,悖论的是,它看起来离文学却差之远矣。读者看不到它有何文学之处,他们根本就不该看到技巧,就这样。
你坚持不肯称之为这本小说的“风格”。
非说有什么风格不可的话,那么就是一种“物理”风格。《情人》是因为我偶然找到一系列照片所衍生出来的,我才开始想到让文字退居二线,凸显影像。可是书写占了先机,动作比我还快,唯有在重新阅读《情人》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建构在借代转喻之上。有的词,譬如“荒漠”“白”“快感”,会跳脱出来,它们在整个叙事中又饶富深意。
现在轮到谈谈你的另一本畅销书了。你认为一本像《痛苦》这样的书,有什么特点?
特点就在于我选择女人面对谈论战争时的恐惧作为叙事观点,而不只是一般的主题。其实书中叙述的是最低下的事实,甚至有关人类生理中最兽性的一面,比如我丈夫从达豪集中营回来时,他那败坏了的身躯;或是那个想跟我上床的盖世太保皮埃尔·拉比耶的故事,我先将他榨干抹净,然后才告发他;或者是那个更加残暴的故事,有人指控我是德国人的奸细,使我遭到严刑拷打。
《痛苦》是本勇敢的小说,恐怖与神圣的混合物,是我写过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针对书中巨细靡遗地描绘了所有事件这点而言,《痛苦》的写作手法很硬、很现代。有人跟我说《痛苦》让他想到巴塔耶。可是《痛苦》不是文学作品,我再说一遍,而是一个或多或少有点像文学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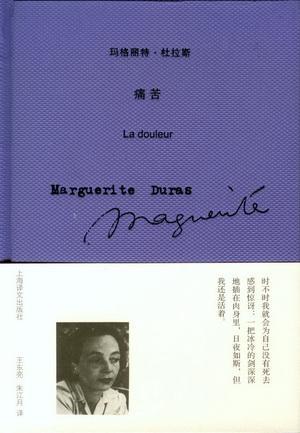
《痛苦》
《痛苦》的写作素材真的来自你二战时记满的笔记本吗?而且它们还真的奇迹般从柜子里面突然冒了出来?
法国许多评论家都不信我。他们要的话,我可以拿我的日记给他们看。我不记得是从哪天开始写的,我只知道都是些草稿、片断、笔记,后来我利用它们写下了《直布罗陀的水手》《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等小说。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在某些事上说谎,可就是这件事不能,一个人没办法在痛苦这件事上说谎。
什么原因促使你出版《物质生活》?这本书是你同意让热罗姆·博儒尔将你的自传式对话录——或者该说你记忆中某些想法的组合——逐字忠实听打下来的记录。
一股欲望,说出我所想的东西、我这一生还从未写过的东西,但它们又令我高兴或担心,一般我在接受访谈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任何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东西。
前些时候,罗布-格里耶谈到有关他自传体作品“传奇故事”中的一部——《昂热丽克或迷醉》、谈到“新自传”,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把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一书的论据发扬光大,并数度援引《情人》为例。他采用“新自传”这种说法来形容自传式作品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并不见得就建立在四平八稳或前后一致的记忆数据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在文字间变幻与飘荡的片断之上,然而这些片断却正好有可能重建靠不住的、可信度低的回忆”。
《萨瓦纳湾》里面有一段:舞台上有名老妇,重新经历着一段混淆不清的过去,然而过去只剩下燃烧着的白石影像。过去混入现在,如此不真实,乃至于有可能变了形,甚至是她自己虚构的。
你在构思最新的这部小说《埃米莉·L》时也遭遇困难。
就是说嘛,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我明明就天赋异禀,可以在一个礼拜内就写出一本书啊……跟我在课堂上写功课一样轻而易举。
我有时候会觉得写《埃米莉·L》的并不是我,我只不过目击了一本书自行完成。其实都是热罗姆的女儿艾琳·兰东,她非要我写完不可。她几乎每天都会到我家来拿稿子,叫人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把打字稿给我看,我再订正。
你自己说过,某些方面《埃米莉·L》跟《劳儿之劫》很像。
区别在于,《埃米莉·L》是一个女人在观察另一个女人发生了什么事,而并未直接牵连进去,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不受影响。其与劳儿·瓦·施泰因所发生的事情正相反,因为事实上,另外一个女人——埃米莉,她是坐在咖啡厅里面的。
就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同时也因为这部小说所涉及的某些主题,《劳儿之劫》被视为你最复杂的一本小说。拉康在他的研讨会专论中,有好几页就是专门献给你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在戒酒。我一直都很怕没有酒精怎么过日子,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加入了这份恐惧。
《劳儿之劫》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一个女人被潜在的爱给逼疯了的故事,这份爱从未表现出来,也从未付诸行动。换句话说,在沙塔拉开舞会的时候,劳儿看到她的未婚夫麦克·理察逊,跟另外一个女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走了,她的一生便将围绕着这种缺乏、这份空无而展开。劳儿是个囚犯,为了自己永远也过不了的生活而疯狂。
你在此处所暗指的“空无”,诚如拉康所言,就是所有生命源由与尽头的“缺乏”。缺乏秩序,缺乏中心,缺乏一个无可救药地被切断联系的“我”,可以找回自我的那个中心。
这倒是真的,我所有的书都是这么产生的,并确切地围绕着一个永远都被召唤、永远都缺乏的框架在移动。
完完全全就是这样。一个不说话、不在场的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那个中国人、直布罗陀的水手、《死亡的疾病》里的那个女人),一个不会发生的事件(譬如《广场》、《黑夜号轮船》、《琴声如诉》、《塔吉尼亚的小马》),故事就可以迸出火花——令人怀想、余音袅袅的故事。
再回头谈谈《劳儿之劫》。你和拉康的关系怎么样?
他一开始就跟我提到弗洛伊德。他声称,从前艺术家在对对象进行研究与分析的时候,都会先从分析入手。我试着向他解释,我并不知道这位劳儿的基因。
毫无疑问,他很看重我,带着男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那种传统态度对女人下评断。
至于我嘛,我不会看他的东西。说真的,我看不太出个所以然来。
你们经常碰面吗?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碰到,他缠着我问东问西,问了两个钟头,我都不太回他,有时候根本就没在听。他说劳儿是临床精神病患的教学案例——老是想起父母双亲与孩子之间原初场景的悲剧——因为他相信可以从这个名字里面找到所有关键。他认为我很聪明地故意帮那个小疯女取的名字:劳儿·V。施泰因,也就是说……我解释一下个中暗藏的密码:“纸翅膀”,再加上意味着“剪刀”的这个V(根据喑哑人士的手语),至于施泰因(Stein),则代表“石头”。拉康综合这些后,很快得出结论:划拳的游戏,也就是“爱的游戏”。他补充说:你是“诱拐者”,我们读者则是“被诱拐者”。
你相信心理分析吗?
我们可以这么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伟大且易懂的作家。至于弗洛伊德学说,则是一门散发着香气的学科,自己绕着自己在打转,跟惯例相比,它使用一种错误的语言,对外面的世界影响越来越少。总归一句,我对精神分析缺乏兴趣。我不认为我有需要,或许也因为我写作的关系才不需要。可是针对心理疾病,我不认为只需要意识到自己神经过敏,它就会痊愈,这是不够的。
自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你已经发行了十五本小说,还没算上电影剧本和戏剧。每次一本书快问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只要还没见天日,每本书都会对自己即将诞生、就快出来了感到害怕。仿佛我们身体里面带着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很累,说他要安静,他要寂寞,他要慢慢来。一旦出来了,这一切皆消失,快如迅雷。
为了变成什么呢?
变成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属于所有将它捧在手中、将它占为己有的人。作家必须把书从书写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让它有生命,可以运行,可以让别人做梦。有人告诉我,有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广岛之恋》。
对,英国超音波乐队唱的。
我很开心,我喜欢大家借用我的作品。
提到《爱》,这本书你换了意大利出版社蒙达多里,而不再是你一贯合作的费尔特里内利和艾奥迪这两家出版社。
谁付我更多钱,我就会更开心。
《爱》这一书名并不独特。
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用这个书名,以对抗所有其他也这么命名的书。《爱》不是个爱情故事,而是有关在激情里面悬而未决的、莫可名状的一切。这本书的意义完全就在于此:省略。
关于写作方面,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说过真的会有“作家撞墙期”,仿佛这是每个作家迟早都会变成受害者的一种情形。你记得自己经历过类似的时刻吗?
我刚刚提过在改编《死亡的疾病》时所度过的危机。总之在一九六八年前,我每天规律地写作,坐在这张桌子前面,就跟别人去办公室上班一样。写着写着,突然,危机发生,几乎整整一年,我的想象力都被卡住。
好不容易《毁灭,她说》终于造访,有如灵光乍现,那时我已经五六天没写了。从那时起,就一直都像这样:得历经长时间、永无休止的沉静,书才能出得来。

